“薩特—加繆之爭”今天還有熱度嗎?兩位男性公共知識分子,兩位卓越的法國文學家,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,一場說不盡的恩怨。事情發生在遙遠的70多年前,但是人物依然新鮮,特別是加繆,《局外人》《鼠疫》的影響力歷久彌新,文字里處處散發的人格和思想依然使人著迷。小說之外,加繆還發表戲劇、散文和思想論著,其中,1951年出版的論著《我反抗,故我們存在》(原書名《反抗者》)最近有了一個新的中譯本,它寫于二人關系由熱轉冷之時,更寫于冷戰開啟前后,一個社會高度分裂的時代。
從加繆的筆記里,能看到《我反抗》的寫作時間是1946年,《鼠疫》在那年出版,但那是個戰爭剛剛結束的冬季,因物資短缺、人心憂傷而顯得格外寒冷。那時,加繆在一個阿爾卑斯山中的旅館住著。他才33歲,已是名作家,也是聲譽達到頂峰的政治左派,可是寫此書時,心情并不好。
“一個人度過了一周,我再一次清楚地認識到,我的能力不足以完成這項工作,一開始時我很狂熱,現在想要放棄。”
這項工作就是寫作《我反抗》。戰爭結束,似乎能松弛一些了,然而加繆眼里已經有了一幅現代圖景:在自由的旗幟下,以正義,以慈愛,以未來,以超人崇拜……以各種名義繼續大肆殺戮。從法國國內的“肅奸”,即肅清在之前4年與德國占領者合作的法國人,導致矯枉過正開始,每個人就都活在一種有毒的政治空氣里,簡而言之,每個人都被要求自證清白。為此,暴力的濫用打開了大門,不能自證者,或是不想自證者,都在暴力的威脅之下。

這是什么情況?加繆在一片含混之中敏銳地看到要點:不管以什么名義,惡的或是善的,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,結果都是暴力被正當化。因此要緊的不是論證對錯善惡,而是停止正在發生的暴力本身。這不需要太多的理論撐腰,而只需要一種樸素的道德感。
在《我反抗》寫不下去的時候,加繆就讀蒙田隨筆。蒙田是16世紀人,可是他的思想從幽深的地下直接射入現實。在蒙田的時代,法國和加繆的時代一樣陷入分裂,不同的宗教教派各舉大旗,討伐敵方,稱其為異端。蒙田有一篇《為雷蒙·塞邦辯護》,很長,經常被拿出來做成單行本。蒙田說,“神圣學說”被無恥地玩弄在各種勢力手中,人們按自己的需要使用它,解讀它,或是拋棄它。蒙田深沉地寫道:人不能超越自己和超越人性,人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觀看,用自己的手來抓取。
我的眼睛看到了暴力,我就要反對它,而不用管這個暴力是打著怎樣的名義——這就是蒙田設下的簡單的標準。加繆認同蒙田的倫理學。他在不同的文學創作里,都寫入了這樣的道德純粹的人,例如《鼠疫》中的塔魯,他在法庭上目睹檢察官父親慷慨斥責一個被告人,非但沒有覺得父親代表公權力的威嚴,反而厭惡不已,因為他眼里沒有“代表”,沒有抽象的“正義”,而只有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凌駕,以及聲音洪亮的暴力訴求。在1949年問世并公演的劇本《正義者》中,加繆更是塑造了年輕的恐怖分子卡利亞耶夫這個角色,他在受命刺殺莫斯科大公的情況下,因為看到大公身邊有孩子,而一念之間沒有下手。
卡利亞耶夫因為自己的心軟遭到同黨的唾棄和懲罰。這是加繆心目中理想的“反抗者”,他要反抗自己眼里的不公平,可是“公平”與否是個抽象觀念,反抗行為最終總要對個體下手,此時,反抗者的行為抉擇就必須訴諸樸素的良知。當他發現自己難以動手時,他落入荒謬處境,目的和行動之間達不成一致,想要實施正義的人得先染污自己的兩手。這種處境導致反抗者的極度厭惡,他繼續反抗,反抗這個無法推翻的處境,承受隨之而來的巨大的孤獨感。
雖然在寫書時遇到困難,但是加繆在戰后的政治知名度一直在上升,他主張反對所有政治暴力。20世紀50年代初,阿爾及利亞開始發生騷亂,作為一個老牌殖民帝國,法國終于也要面對第三世界殖民地獨立浪潮的沖擊。阿爾及利亞出現了慣于搞恐怖活動的民族解放陣線,法國軍隊在當地也實施抓捕,施加臭名昭著的酷刑,對此,加繆寫文章,同時控訴兩者危害平民的暴力。他完全實踐自己的理念,不管薩特怎么看他,怎么嘲諷他幼稚、天真的道德主義。
1951年《我反抗》終于寫完出版。加繆究竟寫了些什么,他是怎么把自己的反暴力理念“上升到理論高度”的呢?
任何哲學思考,都要有一個起點。“反抗”就是加繆的起點。這個起點不可再簡化。笛卡爾的起點是“我思”,先確認一個思想著的“我”是實在的,所謂“我思故我在”;相應的,加繆的箴言是“我反抗,故我們存在”。
為什么反抗是存在的起點呢?加繆說,因為人總歸要意識到荒謬,也就是說,人總歸要意識到自己會死,意識到這個世界對我的生死苦樂無動于衷,意識到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是偶然的,并在成人之后,擁有一個日漸支離破碎的自我。所以,人要通過反抗,來克服荒謬。
于是他做了一份自己的“讀史札記”,從反抗的角度來重看一些節點性的事件、人物和思潮:希臘人,早期基督教,法國革命與薩德侯爵,浪漫主義,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。各種各樣的思潮,從黑格爾、馬克思到尼采,從超現實主義、納粹到布爾什維克。加繆說反抗的力量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增長,進入一種更加絕望的虛無主義,顛覆上帝、取代人類,越來越殘忍地行使權力。這就是“歷史(中)的反抗”,它根源于形而上學的反抗,卻導致了革命——革命企圖用凌駕于世界之上的絕對權力來消滅荒謬。
那么怎樣反抗才是正當的呢?那就是更懂界限、更溫和、更傾向于改良主義的反抗——“學著自己活,也讓別人活,以創造我們的本質”。加繆試圖澄清反抗的基本精神,擯除它被嚴重歪曲的版本,追溯其更加謙和、適度的起源。結合《正義者》來看,加繆理想中的反抗可謂一種秉持貴族操行的行為,“貴族特質就是不問為什么就去奉行美德”。
在《反抗者》即將出版前,加繆和薩特的關系有很大的緩和。因為薩特的戲劇《魔鬼與上帝》正在排演,而女主角瑪麗亞·卡薩雷斯正是加繆的相好。薩特在他的《現代》雜志上刊發了《反抗者》中談尼采的那一章。那確實是雄辯的一章,加繆把尼采的反抗如何被推崇他的人(比如希特勒)轉換為“對惡的歌頌”,細細地說了出來:
“在尼采的思想中,惡只是人面對無法逃避的事物時,傲然接受的一個東西。然而,我們很清楚,他的思想繼承者,以尼采的思想為基礎發展出什么樣的政治。他曾創造出暴君藝術家的形象,但對平庸的人而言,殘暴比藝術來得容易……”
尼采思想被政治暴徒狹隘地利用,“人們借用他的名,反過來讓愚勇扼殺智慧,讓他真正的思想逆轉成全然相反的:觸目驚心的暴力”。雖然這一章被薩特所接受,然而整本《我反抗》的要旨是和薩特的政見相反的,正如《正義者》和《魔鬼與上帝》也是唱反調的。《正義者》呼喚貴族式的反暴力美德,卡利亞耶夫從一個革命恐怖分子轉變為加繆理想中的反抗者,而在《魔鬼與上帝》里,主人公格茨從一個信仰反抗的人,一步步“找到組織”,投身于具體的、暴力的革命。
主動接受暴力,弄臟兩手,就意味著擁抱現實,成為一個不抱幻想的現實的人。在《我反抗》里,加繆明確地把自己同“存在主義者”的陣營劃出了界線,同時向薩特們下了戰書。
這兩位思想領袖的對立,使得1945~1952年間,想要找到方向的法國知識分子都別無選擇,必須表態支持其中的一方。這種情況本身也很荒誕,因為加繆本人最討厭站隊,他一直所持的就是一個中間立場,溫和的,理性的,滲透了貴族道德的。然而他卻被“對標”了,其他人必須要么擁護他,要么反對他,正如他也必須站在一個反薩特的位置上,來樹立自己的道德立場。
此種特殊的情況,也反映在了《我反抗》的語言風格里。加繆的文風,一直是以簡約、動情、精確入微著稱,從《局外人》到《鼠疫》,再到他晚期未能完成的自傳體小說《第一個人》,他的成熟肉眼可見,他的風格中最有趣的特點之一,是一面刻畫貧窮、疾病,刻畫孤獨和單調乏味的生活,一面給人注入一種自然而然的昂揚的熱情,憑此,他也向存在主義的根本命題——生在荒謬世界上的人如何自由地活下去?——給出了一種婉轉的回答。
可是《我反抗》卻不同。這本書里,下判斷的地方非常多,前一句和后一句之間,邏輯關系有時不很清楚。每個句子都是細心推敲過的,都能反映加繆的核心思想,不過,句子和句子之間缺少連接,在本該展開論述的地方,加繆會停下,續上另一個細心推敲過的句子。
這不是一本“娓娓道來”的書,而是一本論戰之書。后來的學者們、傳記作家們,為如何評價這本書而展開爭論,有的人從文字—思想質量本身出發,把它貶為加繆的失敗之作,有的則強調了創作此書需要的勇氣,認為應該把它看作一種可敬的政治行為,而不是一部“作品”。從加繆的筆記,我們可以看到,他一直就以寫了《我反抗》而自豪,他知道自己承擔了多么大的名譽風險:他將不再是一個受到左翼力量推崇的文學英雄,同時,右翼分子因為《我反抗》里對革命暴力的譴責而贊美此書,卻也不會按照加繆本身的成就來承認他的價值。
勇敢固然是勇敢,但加繆所持的那種不可救藥的浪漫的、訴諸貴族傳統的立場,一定無法在那個年代獲得足夠的擁躉。在政治狂熱、立場先行的年代,恪守個體道德良知的加繆,勢必會被孤立。薩特囑咐他的一位追隨者,在《現代》上發表長文,反擊《反抗者》,隨后則是那封著名的絕交信。這些不再贅言。加繆在未來贏得了更多的人心,可是在1954年到他去世的1960年間,眾所周知,他逐漸沉默下去。這是別無選擇的,也是偉大的沉默。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,但是多少對世界看得越來越清楚的人,都走在加繆走過的路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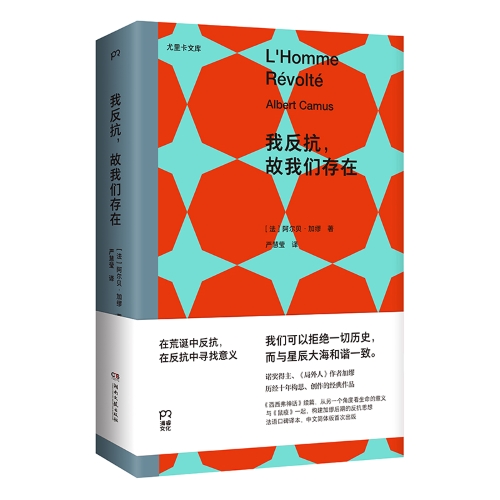
《我反抗,故我們存在》
[法] 阿爾貝·加繆著
湖南文藝出版社·浦睿文化 2025年5月版
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,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