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編者按】2025年6月9日,首屈一指的國際政治驚險小說大師弗雷德里克·福賽斯(Frederick Forsyth)去世,或許標志著一個伴隨冷戰而興起、屬于驚險小說和間諜小說的時代最終落幕。福賽斯前后共創作了十余部長篇驚險、間諜小說,包括《豺狼的日子》《敖德薩檔案》《戰爭猛犬》《魔鬼的抉擇》《第四秘密議定書》《談判高手》《諜海生涯》《上帝的拳頭》《偶像》《復仇者》《阿富汗人》等,每一部都是國際暢銷書,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,也都成為賣座大片。
喜歡弗雷德里克·福賽斯的讀者遍布全世界,他是一位小說家,一個記者,一個當過飛行員的人,他還坦言自己曾受雇于軍情六處。福賽斯很清楚自己的限度,他從來就沒有在文體上有過什么開創性貢獻,他的能力在于寫一個清晰易懂的故事,明快的節奏,扣人心弦的情節安排,讓人一口氣讀到尾——這已足夠他在文學界立足的了。同時他也總是講,自己寫書主要是為了錢。
1971年的《豺狼的日子》是他的處女作,以一次戴高樂遇刺事件為主題,因為賣得好,他再也不用愁錢的事兒了。小說改編成的電影同樣赫赫有名。不過,此作的后續,次年出版的《敖德薩檔案》,對他而言意義更大,因為他的“世界觀”在此作中完全打開并確立下來。一個德國自由記者彼得·米勒,在二戰結束了十多年后,著手調查一個神秘組織,福賽斯巧妙地把這個組織的名字設計為“Organisation der ehemaligen SS-Angeh?rigen”,縮寫成一個讓人浮想聯翩的詞語“ODESSA”——敖德薩。
他把一個看似離奇的構想寫成有理有據的故事。靈感來源,是因為看了一篇1967年7月的報道,報道里提到一些關于納粹覆滅后,那些逃亡的納粹分子的消息,消息來自那位有名的“納粹獵人”——滿天下搜尋追捕納粹分子的神人西蒙·維森塔爾。消息本身虛虛實實:關于阿道夫·艾希曼逃亡阿根廷的事兒是真的,因為艾希曼早在1962年就被引渡回以色列受審處決,而另一些納粹分子跑到美國,參與太空計劃,還有一些隱姓埋名,留在德國。這些人,未必忠于之前的黨派和事業,具有半獨立性,“敖德薩”正是他們用來確立彼此身份的代號。

而在福賽斯的書中,向維森塔爾透露這些秘情的人,是一個不可靠的證人,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:想要攫取納粹黨徒存在瑞士銀行里的大筆財富。福賽斯看到那篇虛虛實實的報道,從中了解到維森塔爾和他的虛虛實實的行動理由后,十分堅定地編成了一個確鑿的故事,他給“敖德薩”組織加上了一個政治目標:推翻新生不久的猶太國家以色列,并且讓彼得·米勒入手調查后,很快遭到追殺。
福賽斯寫得很快。《豺狼的日子》只寫了35天就完成了,一炮而紅之后,出版商敦促著福賽斯趁熱打鐵。那個年頭的出版業正是一臺興旺運轉的機器,福賽斯這樣眼疾手快、腦筋靈活的作者,不成名都說不過去。他在新聞方面的直覺,以及敘述故事的能力,在《敖德薩檔案》里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他把故事的開端設定在了肯尼迪遇刺之后,有點距離感,但又很真實,那些懸疑的片段細致入微,而且極為專業。比如說,米勒躲過了一次汽車炸彈暗殺,原因是他駕駛的那輛捷豹XK150的懸掛系統很緊,剛好卡住了炸彈,使它失效。福賽斯寫來,就好像他真的把炸藥安裝在那個型號的車上,確認它的確不會爆炸一樣。

《豺狼的日子》
弗·福賽斯 著
上海文藝出版社·讀客文化2019年5月版
這樣的細節,使得再挑剔的讀者也會解除武裝。在《豺狼的日子》里,那位打算刺殺戴高樂的殺手“豺狼”,事先踩點時的場景,使人不禁會懷疑福賽斯自己去細細地查探過現場:
“豺狼輕輕地關上門,插好門閂,走完最后半段樓梯后便到達了第六層。在這一層過道的盡頭有一道質量差一些的樓梯通向閣樓。在過道里有兩扇門分別通向兩套面向天井的房間,另外兩扇門通向樓房正面的房間。他的識別方向的能力使他知道這兩套樓房正面的房間都有窗子,可以俯視雷納街,或是側視廣場以及遠處的車站的前院。這些窗子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觀望已久的。
他看看這兩扇門上在電鈴按鈕旁的姓名牌,一塊寫著貝郎瑞小姐,另一塊則寫著夏里埃先生和夫人。他靜聽了一會兒。但是兩間房里都沒有聲音。他檢查了一下門鎖,兩扇門上用的都是彈簧暗鎖,非常結實。這種鎖是法國人最喜歡用的,他們用了這種鎖會有一種安全感……”
引人入勝的小說往往是精確觀察和敘述結合專業度。小說體現了福賽斯的全知全能,他懂情報工作,懂媒體,懂政治格局的“前世今生”,懂軍事國防,懂航空技術,懂遠洋海商……1960年代,他還有一段在尼日利亞東南部比夫拉當記者的經歷,那個地方被一批分離派割據,但沒有建國,福賽斯對這里的環境了如指掌。在《敖德薩檔案》之后出版的《戰爭猛犬》中,有像這樣的段落:
“鉑金是一種金屬,與所有金屬一樣,它也有自己的價格。價格基本上受兩個因素控制:鉑金在國際工業欲完成的某些工藝中的不可或缺性,以及鉑金本身的稀有性。鉑金非常稀有。除了生產商保密的庫存產量外,世界每年的總產量略高于150萬金衡盎司。”
因為小說里的主角想要殺死一名非洲的獨裁者,為的是取到此人國家的鉑金礦產,故而福賽斯堆砌了大量的相關知識。那些對驚險小說這一“類型”本身看不上眼的人,在《戰爭猛犬》面前,對于他對一些最精細的知識的精通無話可說,而轉去吐槽像上述段落透出的一股專業期刊的味道。福賽斯貌似就原樣摘了那些期刊的文章。的確,他在植入這類知識時,往往是不太藝術、不太圓潤的,這也是類型小說常見的缺點。
在選擇反派人物方面,福賽斯也需要動足腦筋,一旦沒選好,他就可能被控誹謗。在寫《敖德薩檔案》時,納粹早已隨著戰敗而被批臭,因此反面人物合該是納粹分子。福賽斯選擇了愛德華·羅施曼,他是著名的“里加屠夫”,1943年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主導了猶太人大屠殺,福賽斯寫書時,他正逃亡在阿根廷,背負了一個反人類罪的罪名。福賽斯顯然從1962年的艾希曼受審中看到,南美會吸引納粹分子,在那里他們有更大的機會得到匿名的保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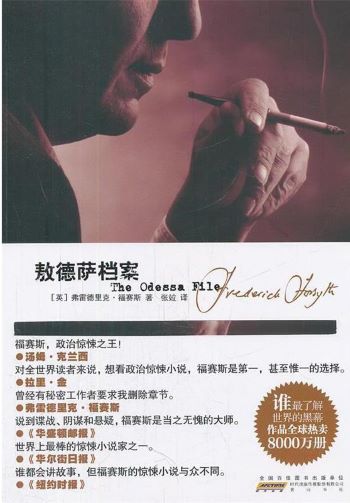
《敖德薩檔案》
[英]弗·福賽斯 著
黃山書社2012年7月版
福賽斯在書中讓他擔任最大反派,并說他已以“弗雷德里克·瓦格納”的假名加入阿根廷籍,這個做法頗可見“富貴險中求”的信念。出版商也是精明得很,他們在宣傳此書時,打出的廣告是“書中的許多人物真實存在,其他人物則真假不明”。宣傳效果是很好的,這本書不到5年,就賣出了百萬冊以上,緊緊追趕《豺狼的日子》的銷量。
《敖德薩檔案》的出版時間也稱得上“時來天地皆同力”。1972年五六月間的慕尼黑奧運會,發生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下屬秘密武裝綁架以色列運動員、警方營救失敗的“慕尼黑慘案”。雖然這只是巧合,可是福賽斯“緊跟時代”的特色一直沒有改變過。1990年后,他立刻寫出像《上帝之拳》這樣的海灣戰爭主題驚險小說,1996年出版的《間諜先生》,切中了人們對蘇聯解體后的“真相”的關心,寫了一大批利用社會急轉中飽私囊的竊國之人。2001年“9·11”之后,他的新故事都圍繞消滅恐怖分子的行動展開。奧薩馬·本·拉登代替了之前的薩達姆·侯賽因,成為大魔頭,不過他們可不會在最后對決中出場,否則就太假了;實際出場的都是他們的代理人——他們都是隨著情節開展逐漸脫穎而出的。
福賽斯和他的小說都問世于一個“大時代”,那個時代的主流敘事是冷戰,是兩大世界級豪強的對峙,而冷戰又是二戰、納粹暴行和大屠殺的后續。他的部分故事,像是《豺狼的日子》和《敖德薩檔案》,都寫在故事實際發生時間的十年以后,看起來很像是經過調查,經過熬時間,相關真相一一浮出水面后才寫成的。就像把礦產開發的知識搬入《戰爭猛犬》一樣,他在如2006年出版的《阿富汗人》這樣的小說中,也會大段地敘述早已成為往事的歷史事實,如蘇聯1980年發動的阿富汗戰爭,有如接觸過了什么解密檔案一般;但他更有一些小說具有前瞻性,比如《間諜先生》的出版,就打破了西方人對俄羅斯可能正享受“和平紅利”的錯覺。

當然,從福賽斯寫小說的才華和風格,都可以追溯到他做過正牌諜報人員的經歷。正因此,他對20世紀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叛徒——一群被稱為“劍橋五人組”的人,為首的是從英國特工投身蘇聯當間諜的金·菲爾比——極為痛恨。1994年,美國中央情報局反間諜官員奧爾德里奇·艾姆斯被揭露長期從事通俄活動,遭到逮捕,被控犯有間諜罪,福賽斯聞訊十分高興。在《間諜先生》里,他用了很大的篇幅,寫這名叛變間諜對于情報機構的破壞,他至少導致了10個美國特工在蘇俄被處決。直到今年6月,86歲的福賽斯去世時,84歲的艾姆斯仍在終身監禁之中。
福賽斯對中央情報局一向是很有意見的,認為它過于傲慢,一直對英國的情報機構頤指氣使,卻后知后覺地意識到,自己內部也出了叛變之人。為此,他在《間諜先生》中脫離了故事主線去說艾姆斯事件,是發泄心中的不滿。在“9·11”之前,他寫過文章談塔利班的情況,他認為,西方人仍然沉浸在冷戰結束后的“歷史終結”情緒里,而情報機構則仍然把目光緊盯沒落的大敵俄國,對來自其他地方、其他文化體系的敵意缺乏警覺。
但在“9·11”之后,福賽斯的態度變了。之前他總忍不住要嘲諷中情局的自大、莽撞,現在他對美國無比同情。他試著寫自己很不擅長的、包含眾多電腦程序操作細節的情報故事,因為他認識到,美國情報機構需要保衛一個比英國面積大得多的國家,他們大量的工作不得不依賴枯燥的技術手段。新世紀之后,福賽斯在美國的名聲大大超過了另一位間諜小說大師約翰·勒卡雷,因為勒卡雷一直反美,態度在“9·11”之后還更為強硬。勒卡雷是個政治自由主義者,福賽斯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保守派。
雖然堅決站在英美捍衛自身安全的一邊,福賽斯在寫反派的時候,還是很聰明地把他們和正統教義區分開來。像是在2006年的《阿富汗人》之類的作品中,那些壞蛋都是機械地執行了他們認為的宗教教義的人,他們的存在并沒有給他們的信仰本身抹黑,福賽斯成功地(當然也是不無套路化地)把他們寫成“世界之癌”,無論他們的行動多么有情可原,都是應該除之而后快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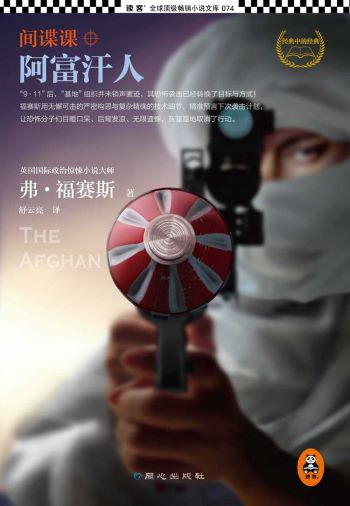
《阿富汗人》
[英]弗·福賽斯 著
同心出版社2013年12月版
今日的俄羅斯和烏克蘭仍在交戰,但世界觀眾們只能通過不時閃入眼簾的一條標題、一個畫面,來得到一個提醒。戰爭,在剛發生時還是一場讓人驚呼“世界越來越壞了”的災難,然后,就漸漸成為一個“小眾”話題,一個像是類型小說一樣,只有關心的人才會關心并追求成為專家的話題。而早在1979年,福賽斯出版的《魔鬼的抉擇》,就把烏克蘭問題推到了讀者面前,在這個故事里,兩個暗殺克格勃高官的烏克蘭自由戰士,劫機逃離蘇聯后,被關押在了西德的監獄里,此事又引起了恐怖分子劫持油輪,而當時的國際背景,是蘇聯即將和美國簽署核不擴散條約,蘇聯提出以索要這兩名烏克蘭人為簽約條件,德國又想要滿足蘇聯人,又在英國、荷蘭的壓力之下不敢這么做,因為油輪若被沉沒會引發環境災難,同時,以色列也插手進來,要接管那兩名烏克蘭人——因為他們本身是猶太人。
雖說情節乃虛構,可是福賽斯對國際政治的復雜性做了很好的呈現。那些實施恐怖行為的人,都有他們不得不這么做的理由,甚至值得同情,但兩個大國之間的核和平,兩名政治犯的生命,還有北海環境亟待保護,這三項都是正當的利益,卻彼此牽制,不可能兼得。福賽斯把故事構造得足夠曲折,雖然最后還是要走驚險小說的路子,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對決,可是,讀過這本書或是這類書的人,也許不再會輕易就政治問題的是非表態了。
福賽斯前作里寫到的人物,會在后作中重出江湖,同樣的人物,在不同作品里的關系會變化。不過,“9·11”之后的他也的確放棄了早期作品里的一些復雜化的取向,轉而明確了他的保守立場,那就是,美英及其盟友們,應當授權特種部隊去追捕那些絕對的惡勢力,如南美洲的毒梟之類不受國際規范約束的“惡棍”。以他的眼光來看,地緣政治是個過于復雜的東西,他自己,作為一個前職業間諜,就是這部復雜無比的機器的一部分,然而進入21世紀后,在一種極為瑣碎化的信息政治環境里,尊重這種復雜性,勢必要把人弄得疲憊不堪,困惑重重。
《豺狼的日子》和《敖德薩檔案》都引領了潮流,無數的追隨者給驚險小說、“納粹反派小說”“偽造身份證件小說”等各種類別添加了新品。在1980年代,他的《談判專家》《第四秘密議定書》里的人物則更加立體一些,福賽斯會為他們及時添上內省。但到了最后幾部作品里,福賽斯的人物的形象就明顯比以前更扁平了,他的個人精力畢竟已過巔峰,進入21世紀以后,驚險小說這一類型的能量,在間諜、大國博弈、地緣政治這類題材里也漸漸退去了。
幫企客致力于為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財經資訊,想了解更多行業動態,歡迎關注本站。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,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