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編者按】從1865年至1915年,英國與荷蘭在東南亞劃分了各自的殖民范圍,開辟出新的邊界線。然而,這一過程卻助長了由鴉片販子、假幣走私者、人販子和軍火商組成的龐大地下經(jīng)濟(jì)網(wǎng)絡(luò),邊境地帶的走私活動(dòng)尤為活躍。
在《滲透邊界的秘密貿(mào)易》中,美國康奈爾大學(xué)歷史學(xué)系教授埃里克·塔利亞科佐通過深入研究報(bào)刊雜志、旅行日記、司法檔案、歷史影像、航海日志、國際條約以及口述歷史等史料,展示了英荷殖民國家形成期間,統(tǒng)治力量與走私者在邊境地帶進(jìn)行的激烈較量。在此過程中,普通民眾、合法商人、走私者與海盜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,合法與非法活動(dòng)、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(guān)系也呈現(xiàn)出錯(cuò)綜復(fù)雜的面貌。時(shí)至今日,走私仍然是一些東南亞國家邊境生活的一部分,走私者與國家之間的博弈未有止息。盡管邊境常常被嚴(yán)格管控,但總有人試圖突破限制。因?yàn)椋瑢?quán)力、道德和利益的追求從未停息。
經(jīng)出版社授權(quán),第一財(cái)經(jīng)節(jié)選了書中部分篇章以饗讀者。
東南亞這一地區(qū)的走私活動(dòng),以及不同形態(tài)的國家或初具國家形態(tài)的政治體試圖阻止走私的歷史,可以追溯到該地區(qū)過去的幾個(gè)世紀(jì)。這一地區(qū)的早期文明沒有明確的邊境和邊界,因此也就不存在非法跨越。相反,這些早期文明,特別是在大陸上,多以曼陀羅(mandalas)的形式存在,有一個(gè)擁有強(qiáng)大權(quán)威的地理核心,以逐漸減弱的方式向外輻射,直至完全得不到有效的效忠。在東南亞島國,一種伴隨而來的模式是在河口上建立小王國,此類王國的權(quán)力部分來自控制貿(mào)易的嘗試,尤其是對上下游(在馬來語里,上下游分別是“hulu”和“hilir”)產(chǎn)品征稅。這兩種組織形式都為走私活動(dòng)留出了空間。東南亞第一個(gè)偉大的海洋文明三佛齊王國(Srivijaya,又作“室利佛逝”,公元7世紀(jì)至12世紀(jì)),其繁榮便主要建立在壟斷馬六甲海峽的貿(mào)易上。這個(gè)王國在馬六甲海峽的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兩側(cè)都設(shè)有前哨,因此能夠迫使經(jīng)過船只接受強(qiáng)制征稅,這一政策促使了有能力避免繳稅的商人開展違禁品貿(mào)易。幾個(gè)世紀(jì)后,繼三佛齊王國之后,馬六甲蘇丹國(Melaka Sultanate)成為這片水域的最高權(quán)力中心,它從這一經(jīng)驗(yàn)中汲取教訓(xùn),將關(guān)稅和港口稅保持在較低水平,試圖鼓勵(lì)大量貿(mào)易。然而,由于馬六甲(位于今天的馬來西亞)成為一個(gè)著名的中轉(zhuǎn)站,用于運(yùn)輸價(jià)值與體積/重量比非常高的貨物,包括金粉、寶石、香料和“異域藥材”,因此可以假設(shè),這些貿(mào)易中也存在相當(dāng)數(shù)量的走私活動(dòng)。
然而,隨著17世紀(jì)荷蘭人的出現(xiàn),這些模式中有一些開始發(fā)生變化。荷蘭東印度公司(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,簡稱“VOC”)試圖制定嚴(yán)厲的強(qiáng)制壟斷政策(尤其是在香料的生產(chǎn)和運(yùn)輸上),確保其在東印度群島(今印度尼西亞)部分占領(lǐng)地區(qū)的利潤。在印度尼西亞東部,特別是在馬魯古(Maluku,過去被稱為香料群島),這些政策包括大肆謀殺某些生產(chǎn)丁香和肉豆蔻的島嶼上的居民、將之驅(qū)逐出境,以及武裝監(jiān)視香料園,以確保這些商品不會被走私出去,從而對荷蘭的壟斷企業(yè)造成經(jīng)濟(jì)損失。在18和19世紀(jì)的印度尼西亞西部,荷蘭人還對邦加島和勿里洞島(Belitung)的錫的自由貿(mào)易采取了打壓舉措,這促使居民嘗試把礦石偷偷地賣給路過的英國商船和中國帆船。在東部水域,荷屬東印度群島首府巴達(dá)維亞外的某些海灣和溪流以走私者聚集地而聞名。當(dāng)然,這些午夜交易的部分主要參與者,本身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里報(bào)酬微薄的職員,他們在自己首府的眼皮底下討價(jià)還價(jià)。
到了19世紀(jì)初的前后幾十年,一些政治地理格局已經(jīng)逐漸得到鞏固。1769年,英國人占領(lǐng)了北婆羅洲北端的巴蘭邦(Balambangan)岸島;1786年,馬六甲海峽北端的檳城也遭吞并。1819年,斯坦福德·萊佛士(Stamford Raffles)爵士買下新加坡的著名舉動(dòng),將這兩個(gè)早期的前哨地區(qū)一分為二,開始顯示出日后劃分整個(gè)東南亞諸島英荷邊界的“項(xiàng)鏈”輪廓。1824年的一項(xiàng)重要條約首次將海峽一分為二,英荷雙方交換了各自在對面的領(lǐng)土,但在這片新興的邊疆地帶,貿(mào)易和影響力仍持續(xù)快速發(fā)展。19世紀(jì)40年代初,英國冒險(xiǎn)家詹姆斯·布魯克(James Brooke)在婆羅洲西部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國;巴達(dá)維亞密切關(guān)注著這一舉動(dòng),對其影響深感不安。19世紀(jì)40年代,英國王室占領(lǐng)了西婆羅洲海岸以北的納閩島。1851年,其他冒險(xiǎn)家[比如美國人吉布森(Gibson)在占碑(Jmabi)的舉動(dòng)]試圖沿著這片快速發(fā)展的邊疆開辟獨(dú)立的小領(lǐng)地,荷蘭人對此非常焦慮。最終,1871年,兩個(gè)殖民大國再次來到談判桌前,劃定各自的勢力范圍。倫敦承認(rèn)蘇門答臘完全是荷蘭的領(lǐng)地,以換取在近年來得以鞏固的海上邊界上實(shí)現(xiàn)商業(yè)權(quán)利的保障。兩年后,荷蘭人襲擊了亞齊蘇丹國,隨后開啟了征服亞齊蘇丹國的進(jìn)程。亞齊蘇丹國是邊境沿線最后一個(gè)有一定規(guī)模的獨(dú)立政治體。一年之后,也就是1874年,英國人在馬來半島開始“前進(jìn)運(yùn)動(dòng)”(Forward Movement),將他們的勢力和影響擴(kuò)大到了霹靂州(Perak)。
在東南亞塑造這一新興的英荷邊疆,需要許多鋪墊的過程。1865年至1915年期間,繪制邊境地圖的各種任務(wù),包括勘探、實(shí)地測量,然后將所得數(shù)據(jù)分類為兩個(gè)殖民地國家能夠處理和理解的形式,一直在推進(jìn)。有關(guān)帝國主義發(fā)展軌跡的學(xué)術(shù)經(jīng)典提供了一套寬泛的概念框架,用于研究這些被劃定的邊境是如何落實(shí)和執(zhí)行的。只有相對較少的作者著眼于對英國這一側(cè)開展分析工作;印度總是比東南亞更能引起英國帝國史學(xué)家的關(guān)注。總體而言,關(guān)于荷蘭帝國主義在東印度群島的著述要多得多,也更具爭議性。一些作者質(zhì)疑荷蘭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項(xiàng)目是否存在本質(zhì)上的不同,這一質(zhì)疑引發(fā)了激烈的辯論。盡管此類討論在20世紀(jì)70年代就開始了,但近年來,對話中又加入了一些重要的研究,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對荷蘭外交政策的新修正主義研究。很遺憾,將這一課題納入更大的帝國主義主題之下的最優(yōu)秀的學(xué)術(shù)研究大部分都是用荷蘭語寫的。
如果說,東南亞諸島的邊境形成,是通過歐洲軍事力量的脅迫實(shí)現(xiàn)的,那么也可以說,它是通過持久而復(fù)雜的測繪項(xiàng)目來完成的。一些重要的學(xué)術(shù)工作研究了該地區(qū)的這些過程,盡管這方面最詳盡的文獻(xiàn)仍然只有荷蘭語版本。然而,關(guān)于東南亞殖民地邊境形成的概念演變,最佳研究代表作是通猜·威尼差恭(Thongchai Winichakul)洞見犀利的《圖繪暹羅》(Siam Mapped),但均未涉及南島語族(Austronesian)的世界。而這本書中所描述的地理和認(rèn)識論過程,也尚未在該世界的島嶼和海峽中找到對應(yīng)情形。目前,也還沒有人基于近年來對近代早期歐洲已趨成熟的研究思路,解釋邊疆地區(qū)國家的形成。這很令人感到遺憾,因?yàn)闅W洲歷史所描述的國家支持的暴力過程,恰恰是西方在世界其他地方擴(kuò)張動(dòng)態(tài)的前身。這在東南亞尤其如此,因?yàn)檫@個(gè)地區(qū)和歐洲一樣,由許多小規(guī)模或中等規(guī)模的政治體構(gòu)成,它們的邊境領(lǐng)土彼此接壤,有時(shí)甚至重疊。
隨著學(xué)者們著手研究不同地區(qū)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經(jīng)歷往往相似的過程,關(guān)于邊境如何形成的概念性研究已然成為一個(gè)龐大而復(fù)雜的領(lǐng)域。例如,通過分析加拿大五大湖周圍的毛皮貿(mào)易史,我們可以為分析東南亞地區(qū)提供經(jīng)驗(yàn);而圣彼得堡對俄羅斯遠(yuǎn)東地區(qū)巨大木材儲備的推動(dòng),從資源的角度來看也對東南亞研究有著指導(dǎo)意義。在中國,遙遠(yuǎn)的西部省份新疆和甘肅常常充當(dāng)?shù)蹏牧鞣诺兀趤嗰R遜地區(qū),巴西在邊疆開發(fā)橡膠的活動(dòng)不斷擴(kuò)大,許多當(dāng)?shù)厝藙e無選擇,只能參與到該地區(qū)的經(jīng)濟(jì)活動(dòng)中。歷史學(xué)家試圖追蹤病原體在外圍人口中的流動(dòng),也順帶研究了印度的疾病及其與邊境地區(qū)的關(guān)系。不管討論的對象是資源、政治還是當(dāng)?shù)孛褡宓娜诤希羞@些全球邊疆環(huán)境都與東南亞新興的英荷邊界存在相似之處。一些學(xué)者已經(jīng)開始跨越時(shí)間和空間,比較不相關(guān)的邊境地區(qū)的經(jīng)歷和環(huán)境;他們的結(jié)論既有趣又令人驚訝,而且涉及文化、政治和農(nóng)村經(jīng)濟(jì)。其他作者也參與了這場辯論,他們著眼于比利牛斯山的邊境村莊、世界范圍內(nèi)不同邊疆的身份認(rèn)同問題,以及著名的特納(Turner)美國西部邊疆理論的修正及其重要的知識遺產(chǎn)。
然而,較之對世界其他地區(qū)的研究,對英荷東南亞殖民地區(qū)之間新出現(xiàn)的邊界的研究直到最近仍落后一步。20世紀(jì)60年代末出版了有關(guān)婆羅洲和北蘇門答臘島邊疆方面的扎實(shí)著作。但怎樣研究邊境的觀念,自那以后發(fā)生了重大變化。只是在過去15年里,才陸續(xù)有一些研究從各種新的角度,審視局部邊界形成的特定方面。這些嘗試包括分析區(qū)域本土勢力與巴達(dá)維亞之間微妙的、不斷變化的關(guān)系,以及論述所謂的荷屬東印度群島外島經(jīng)濟(jì)的令人興奮的新工作。還有一些研究[特別是對荷蘭皇家郵船公司(Koninklijke Paketvaart Maatschappij,簡稱“KPM”)及印度尼西亞島嶼間航運(yùn)業(yè)的研究]表明,在周邊地區(qū)國家的形成中作為組成部分的海洋,往往把邊疆與“中央”拉得更近了。這在東印度群島尤其重要,因?yàn)橛⒑蛇吔拇蟛糠纸尤赖貐^(qū)都為水域而非陸域。馬六甲海峽又淺又狹窄,隔水相望的兩岸陸地上的居民擁有相似的語言、種族和宗教,這對劃定國際分界線而言并不理想。事實(shí)上,貿(mào)易和移民在海峽兩岸已經(jīng)互相滲透了至少2000年,這也給任何嘗試劃定邊界的人帶來了問題。下面的篇幅,將詳細(xì)討論這些對邊境的固化以及邊界形成過程的挑戰(zhàn)。
上文提到的政治進(jìn)步所創(chuàng)造的經(jīng)濟(jì)世界,在19世紀(jì)末和20世紀(jì)初也是一個(gè)截然不同、對比鮮明的世界。在新出現(xiàn)邊界的英國一側(cè),馬來亞西海岸通過殖民地種植園(特別是橡膠和油棕種植園)以及錫礦(在馬來半島的錫礦開采歷史可追溯到殖民前的時(shí)代)迅速成為財(cái)富的來源。沙撈越(Sarawak)和英屬北婆羅洲(分別由布魯克家族和北婆羅洲公司經(jīng)營),最終也成為高資源驅(qū)動(dòng)型經(jīng)營單位,盡管時(shí)間比馬來半島晚。然而,沿著婆羅洲邊境,仍然有大片森林將英國和荷蘭的勢力范圍分割開來,遠(yuǎn)離英屬一側(cè)蓬勃發(fā)展的礦區(qū)和種植園世界。在荷屬東印度群島,大部分邊境居民區(qū)的經(jīng)濟(jì)通常被描述為二元經(jīng)濟(jì)的證據(jù):荷蘭的資本密集型農(nóng)業(yè)和采掘業(yè),與當(dāng)?shù)厣a(chǎn)者的鄉(xiāng)村經(jīng)濟(jì)。在這種對外島的描述中,當(dāng)?shù)鼐用竦慕?jīng)濟(jì)世界與其殖民統(tǒng)治者的經(jīng)濟(jì)世界之間少有交集。然而,新近的研究表明,在荷屬殖民地首府、當(dāng)?shù)厣a(chǎn)者和諸如新加坡等地區(qū)港口連接成的一張錯(cuò)綜復(fù)雜的網(wǎng)絡(luò)中,邊境居民之間實(shí)際上存在著怎樣復(fù)雜的經(jīng)濟(jì)互動(dòng)和相互影響。因此,邊境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經(jīng)濟(jì)聯(lián)系非常微妙,巴達(dá)維亞和泗水(Surabaya)等殖民中心彼此之間的聯(lián)系、它們與海峽殖民地等其他殖民前哨之間的聯(lián)系,都是多種多樣、非常復(fù)雜的。
(本文節(jié)選自《滲透邊界的秘密貿(mào)易》第一章《導(dǎo)言》中《不斷演變的空間網(wǎng)格》部分,標(biāo)題為編者所擬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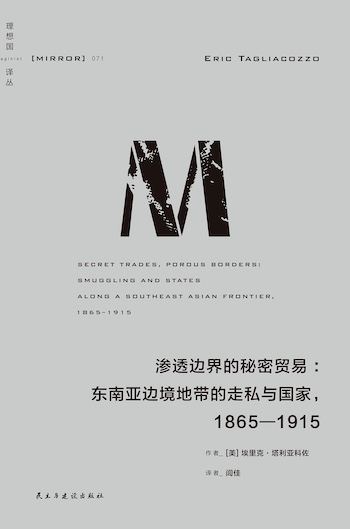
《滲透邊界的秘密貿(mào)易》
[美] 埃里克·塔利亞科佐 著 閭佳 譯
理想國·民主與建設(shè)出版社 2025年2月
幫企客致力于為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財(cái)經(jīng)資訊,想了解更多行業(yè)動(dòng)態(tài),歡迎關(guān)注本站。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(quán)歸原作者所有,轉(zhuǎn)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標(biāo)記有誤,請第一時(shí)間聯(lián)系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



